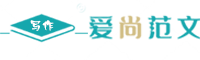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文化论文【经典3篇】
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文化论文 篇一
夏王朝始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夏王朝始年,指的是传说中的夏朝建立者夏禹在位的时期,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的诞生。夏王朝始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夏王朝始年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夏禹在位时,夏朝人民开始使用符号和记号来记录文字,这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夏王朝始年的文字记载,不仅使历史事件得以被记录下来,也使后世人们能够通过文字了解和研究夏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夏禹的文字记载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夏王朝始年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夏禹被认为是夏朝的开国君主,他在位期间,秉持了崇尚德行和治国有道的理念。夏禹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努力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夏王朝始年的文化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夏王朝始年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它对后世王朝的影响。夏禹在位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对后来的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王朝始年的一些制度和思想,被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朝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对后来的商、周等王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特点。
总之,夏王朝始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对后世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王朝始年的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演变过程,对于我们认识和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文化论文 篇二
夏王朝始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夏禹作为夏朝的开国君主,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夏王朝始年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开端。夏禹在位时期,夏朝的社会制度逐渐形成,人们开始建立起了封建王朝的基本制度和思维模式。夏王朝始年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开始,为后来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夏禹在位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夏王朝始年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它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夏禹在位期间,提倡崇尚德行和治国有道的理念,强调君臣之间的忠诚和义务。夏王朝始年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夏禹的治国思想和道德观念,对后来的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夏王朝始年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它对后世王朝的影响。夏禹在位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对后来的王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夏朝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被后来的商、周等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夏王朝始年的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和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夏王朝始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夏禹在位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王朝始年的研究和思考,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认识和传承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文化论文 篇三
关于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文化论文
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夏王朝开始建立的年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没有形成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统一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建立夏代年代学基本框架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设计了“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研究”、“《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和“《夏小正》星象和年代研究”四个专题。此外,与此相关尚有文献学领域的有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研究和历史学领域的文献中夏代积年和各王年代研究等专题。希望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出一个科学有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建立夏代年代学的基本框架,推定夏代的始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从考古学上找到夏文化,确认夏、商文化的分界和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早期夏文化,这是解决夏年代问题的前提。
通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二里头等相关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基本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关于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早期夏文化,仍存在着分歧。我曾经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的观点,并表示赞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是早期夏文化的意见。我认为,以登封王城岗晚期遗存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始建是夏商分界的界标应该成为夏王朝始年推定的考古学基础。
当然,谁都知道,考古学只能解决相对年代,现代测年技术和其它学科才有可能提出绝对年代。十分可喜的是,测年学家通过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及登封王城岗遗址采集的含碳样品的判定,提供出了一大批对研究夏年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与文献学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对夏王朝始年提出一个有倾向性的意见是完全可能的。
夏王朝从禹开始共有十四世十七王,这在《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很清楚,而且向无疑义。关于夏代的总积年,古代文献也有记载,主要有两说:一说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代表,“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另一说以《易纬·稽览图》为代表,“禹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两说相差整40年。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古本竹书纪年》可能包括了少康在野亡命致使王位空缺的所谓“无王”时期,而《易纬·稽览图》则不包括这一时段。从禹受舜禅至桀亡的夏代总积年为471年说可作为推定夏代始年的重要参考。
商王朝从汤到纣共17世30王,如含未立而卒的汤之子大丁则为31王。《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所记商世系已基本为甲骨卜辞所证实。关于商代的总积年,古文献明确提到的确切年数的有三说:《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鬻子》:“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而近于六百年说的有《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近于五百余年说的有《孟子·尽心下》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世经》之629年说,乃刘歆据《三统历》推得,不见于先秦文献,又无可靠根据,难以凭信。
496年说出于《古本竹书纪年》,可信度理应较大,但其明言29王,则与已为地下出土甲骨文证实的商有30王(含汤子大丁为31王)相矛盾。况且,同样据《古本竹书纪年》商后期8代273年与商前期9代仅有223年(496年减去273年)亦太过悬殊,其真实性自然很可怀疑。
《鬻子》在《汉书·艺文志》虽列为小说家类,但比较起来,其所记之576年则很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这不仅是因为有《孟子·尽心下》之“五百有余岁”的支持,而且576年除以17世所得的每世平均年数也与取夏积年471年除以14世所得之平均年数及商后期273年除以8世所得之平均年数相接近。
研究商年的学者,多倾向认为商积年在550年左右较为合理。陈梦家先生在《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怀疑“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中之“汤灭夏以至于受”很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他认为《纪年》的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而“自汤数至文丁是二十九王,没有帝乙、帝辛。”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商末三王年代的推定,帝乙约26年,帝辛约30年。果如此,则商代总积年约为496年加上56年所得之552年,这与《鬻子》之576年相差只有24年。
如取夏积年471年,加商积年之576年或552年,可求得夏商总年数约为1047年或1023年。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之最佳方案,由此可得夏王朝之始年为1046(年)加1047(年)之前2093年或1046(年)加1023(年)之前2069年。
以上两个结果主要是从有关文献记载的研究推出,究竟是否合理,何者更接近历史之真实年代,可以通过与有关碳十四测定数据的整合加以检验。
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测有如下数据:
王城岗二期之告西T157奠基坑6为:2124-2088BC;
王城岗二期之告西T179奠基坑8为:2123-2087BC;
王城岗三期之告西T31H92为:2092-2044BC;
王城岗三期之告西T179H470为:2086-2044BC;
将主要依据文献研究推定的结果和碳十四测定的结果相对照,前2093落在王城岗二期年代范围之内,前2069年则落在王城岗三期年代范围之内。二期王城岗古城开始建造,三期是其主要使用时期,三期以后,古城就废弃不用了。我赞同安金槐先生有关王城岗古城可能是文献中的“禹都阳城”的阳城遗址的意见,如以王城岗古城的始建作为夏王朝建立的界标,那么,取商积年576年,夏积年471年,由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046年)前推所得之公元前2093年则可作为夏王朝的始年。如按我曾推测的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那么取商积年552年,夏积年471年,由武王伐纣之内前推所得之2069年则可作为夏王朝的始年。
从文献研究推定的结果和碳十四测定的有关数据的整合可以看出,两者较比接近,表明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学上的推定并非毫无根据。夏王朝的`建立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应该是可信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前2093年和前2069年两个结果中再作出进一步的选择。
推求夏王朝的始年,与夏商的分界之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对前面的推定再做一次检验。
根据文献学研究结果,以武王伐纣之年在前1046年为基点,取商积年为576年,则夏商分界在前1622年;取商积年552年,则夏商分界在前1598年。
考古学上,多数学者已经认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二者的始建均可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两座商城采集的标本有如下的测定数据: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之C1H9:25(卜骨)为:1616-1546BC;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之98T232夯土VII(木炭)为:1618-1537BC;
偃师商城一期二段之98YSJ1D2T1009G3(木炭)为:1621-1524BC;
应该说这三个数据是基本一致的。如以此与依据文献记载推出的夏商分界的两个结果即前1622和前1598年相校,显然它更支持取武王伐纣前1046年、取商积年552年推得的夏商分界之年前1598年。1598年加上夏代积年471年为2069年。
取夏之始年为公元前2069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仲康日食研究”专题的研究结论也不矛盾。《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有关内容和《史记·夏本纪》所记“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学者多认为是发生在夏代仲康元年季秋的一次大食分日食,倍受国内外天文学史家的关注。“仲康日食研究”专题的学者认为,将“季秋”的范围稍微扩大,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73年至1850年共423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古本竹书纪年》记禹45年、启39年(或29年),《今本竹书纪年》记太康4年,三王合计88年。由2069年减去88年为1981年,次年,即公元前1980年为仲康元年。这与洛阳地区符合“季秋”的11次大食分日食中的前2019年12月6日相差39年,与前1970年11月5日的一次相差仅十年,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尽管文献对禹、启、太康在位年的记载是否确有所本,我们无从查考,但将前1970年11月5日的一次日食作为推求夏王朝始年的参考,不能说是毫无意义。至少二者并不发生不可解释的矛盾。
此外,《墨子·非攻下》在论及舜命禹征三苗时有“昔者三苗大乱,天命亟之。日妖宵出”语,有学者认为所谓“日妖宵出”可能也是一次“天再昏”或“天再旦”的日食现象。“夏商周断代工程”之“禹伐三苗”专题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计算远古日食,得出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大食分日食有4次,即前2097年8月31日“天再旦”、前2075年6月30日“天再昏”、前2072年4月20日“天再昏”和前2029年7月1日“天再旦”。在这四次中,除去前2029年7月1日的一次过晚,其它三次均有可能,它们发生的时间均在禹受舜禅的前夕,这一结果也可作为推定夏始年的参考。
与推定夏代始年有关,尚有纬书中所谓“五星联珠”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有“

总括以上研究成果,我认为如以禹之受禅为夏王朝的开始,则夏王朝的始年应在公元前21世纪前期,大体就在前2069年前后,不会早到公元前22世纪,也不能晚到公元前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