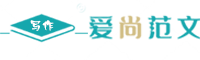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精简3篇】
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篇一
朱彝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之一,对于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对《花闻集》和《草堂诗馀》的接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共词学观的重视。
共词学观是指诗歌创作中词语之间的共通性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朱彝尊在他的评论中多次提到了共词学观,并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他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应该是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通过共同的意义或感情来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他认为,诗歌的共词学观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语言游戏,而是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花闻集》中,朱彝尊对诗人的词语运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诗人通过精细的语言表达和运用,使诗歌中的词语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富有韵律和美感的整体。他特别强调了《花闻集》中的共词学观对于诗歌表达的重要性,认为诗人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而在《草堂诗馀》中,朱彝尊对诗人的共词学观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通过共同的意义和感情来传达诗人的思想和情感。他指出,《草堂诗馀》中的共词学观是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诗人可以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总的来说,朱彝尊对《花闻集》和《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的观点是积极肯定的。他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应该是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通过共同的意义或感情来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他认为,共词学观是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朱彝尊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古代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篇二
朱彝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之一,他对于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见解深受后人推崇。在他对《花闻集》和《草堂诗馀》的接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共词学观的认可和推崇。
共词学观是指诗歌创作中词语之间的共通性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朱彝尊在他的评论中多次提到了共词学观,并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他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应该是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通过共同的意义或感情来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他认为,共词学观是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提高诗歌的艺术性和表达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花闻集》中,朱彝尊赞赏了诗人对共词学观的运用。他认为,诗人通过精细的语言表达和运用,使诗歌中的词语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富有韵律和美感的整体。他特别强调了《花闻集》中的共词学观对于诗歌表达的重要性,认为诗人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而在《草堂诗馀》中,朱彝尊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诗人的共词学观。他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通过共同的意义和感情来传达诗人的思想和情感。他指出,《草堂诗馀》中的共词学观是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诗人可以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通过对朱彝尊对《花闻集》和《草堂诗馀》的接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共词学观的认可和推崇。他认为,共词学观是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古代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篇三
关于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摘要]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论文关键词]《花间集》;《草堂诗馀》;文学批评;朱彝尊;词学观
《花间集》和《草堂诗馀》(以下简称《花间》和《草堂》)是唐宋两个不同时期的选本。在词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审美倾向和标准影响了一代文学风尚,还导致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本文通过梳理清初词人朱彝尊对这两部选本的不同态度,探窥其词学观。
一、朱彝尊之前词坛对《花间》《草堂》的态度
形成于晚明的云间词派以《花间》为宗,对《花间》《草堂》可谓全盘接受;而后的扬州词派摆脱前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念,给予这两部选本较合理的定位,做到兼容并蓄,同时给予一定的反思;到阳羡派时,开始真正将明词的衰微归之于《花间》《草堂》,清初词风在不断转变.逐渐从柔婉走向走向雄浑。但是词风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至朱彝尊时,便不余遗力批明词、扫《草堂》,在对《花间》《草堂》的不同批评中建立自己的词学观。
二、朱彝尊对《花间》《草堂》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词学理论
朱彝尊对《草堂》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深恶痛绝。以下引录他的有关论述如次。古时选本,若《家晏集》……皆佚不传,独《草堂诗馀》所收最下最传。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馀》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桔”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也。
《花问》体制,调即是题。如“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是也。宋人词集大约无题,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
——《词综·发凡》¨
词虽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
——《孟彦林词序》
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陋习。
——《词苑萃编》卷八引

在朱彝尊看来,《草堂》有如下弊病:第一,为“便歌”而分类的俗。朱氏抨击“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他认为,《草堂》为优伶狎客所好,流行于歌楼酒榭,非文人雅士之趣,低俗不堪。第二,语言陈旧俚俗。
“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同时,朱氏还批判明词:“陈言秽语,俗气薰人骨髓,殆不可医”(《词综·发凡》),可谓批《草堂》的佐证。第三,内涵浅陋。他赞扬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之陋习”,实则批草堂词不淡雅、无寄托遥深。
那么,朱氏欲将词引向何方?既然《草堂》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俗”字,他要建立词的审美倾向当然是与“俗”相反的“雅”词。
1.推举雅词选本
朱彝尊推举的'选本可从他的如下论述中摘出曩见鸡泽殷伯岩、曲周王湛求、永年中和盂随叔言作长短句,必日雅词,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篇,《草堂诗馀》可废矣。
——《乐府雅词跋》
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瑾《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书绝妙好词后》
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
《花间》、《尊前》而后,言词者多主曾端伯所录《乐府雅词》。今江淮以北称倚声者辄日:“雅词”。甚矣,词之当合乎雅矣!自《草堂》选本行,不善学者流而俗不可医。读《秋屏词》,尽洗铅华,独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遗音,此有井水饮处所必歌也。
——《秋屏词题辞》
《乐府雅词》专收北宋一代词人词作,而柳永苏轼两位具代表性风格的大家都未揽入,证实曾健在《乐府雅词引》中所说的“删除…‘艳曲”、“涉谐谑则去之”的批评标准,表现出崇雅黜艳、崇雅黜俗的词学观。《绝妙好词》则以立派为宗旨周密只着眼予清雅婉丽之篇。朱彝尊大力推举这两部词选,便是为使时人摆脱《草堂》陋习,走上学习雅词选本上来。同时,他和汪森共同选辑《词综》,也意在为人们提供比较好的学习师法范本他在“订《词综》付雕刻”后所作《摸鱼子》中就欣然写道:“别裁乐府。谱渔黄洲,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明代流行、清初多数词人崇尚的《花间集》,在朱彝尊词学批评中,没有遭到与《草堂》同样的命运。相反,朱氏认为《花间》是与《草堂》相对立的,如:“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陋”,甚至认为《花间》与《乐府雅词》一样“合乎雅矣”,赞扬“《花间》体制,调即是题”,为文人雅士所诵,到《草堂》时,则“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流为优伶狎客之娱,“深为可憎”。从朱氏推举的三部词选可看出他雅词的审美轮廓:一是艳而不俗;二是超远清虚;三是寄托人品,内涵深遥。
2.提出雅词的标准——雅正
朱氏在《群雅集序》中指出:“昔贤论词,必出雅正,是故曾储录《雅词》,鲷阳居士辑《复雅》也”。《乐府雅词跋》也说:“盖词以雅为尚。”
虽然朱彝尊没有明确雅正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前人对雅正的解释和他的有关论述中归纳出来。如: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 ——《静惕堂词序》
词的传统主题一般都是披风抹月,伤春悲秋,儿女相悦之情,在这传统主题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托,是朱彝尊于清初,继陈子龙、邹祗谟等之后提出。《离骚》以香草引类警喻,《诗经》中的变雅之作,是王道由盛变衰后的作品,一般都是刺诗,运用赋比兴的手法,通过“主文谲谏”达到怨刺上政,从而产生温柔敦厚。这些手法用于词中则是“意内言外”,即言情之词与传统诗教相结合,反映社会现实,“鼓吹元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中正醇和。朱彝尊的目的就是通过比兴手法,将词拉向诗教的轨道。同时,他推论词的源头,进一步阐述词与诗功能的相同:“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旬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尔。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水村琴趣序》)南风歌、五子歌均有其严肃的主题,是诗歌中的“大道”,今朱氏以之与词相提并论,更抬高了词的诗教功能,也抬高了词的地位,使它融人了儒家正统文学的血液。
3.推尊南宋雅词
朱彝尊提出著名的观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及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发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工极变的南宋词,不是泛指一切词。既不包括俚俗的艳词,也不包括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而专指南宋雅词,李康化先生认为是专指宋末临安词人之词’’。南宋的雅词与北宋雅词不同,北宋雅词浑涵,词淡而情浓,有高远之姿,南宋雅词深美,文丽而情隐,有妍雅之态)。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词中,为何选择南宋雅词?曹保合先生在《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他认为,南宋雅词在创作队伍、创作技巧、雅词的开拓、雅词的理论远远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词偏裱挚,南宋雅词偏清空,而朱氏喜欢的是偏清空的雅词,即汪森所说醇雅。既要保持词自身委婉抒情特点,又能够有所寄托。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同时略作补充,朱彝尊选择南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赵宋王朝与朱明王朝都是上被异族征服的汉族政权,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出于对故国、对日君的眷恋,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朱氏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同时,朱彝尊在《书花间集后》文中云:“方兵戈傲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处时代文网之密,文字之间如有择词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发现,则被定罪,受尽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浑苍茫的词风逐渐隐去,文人开始寻求“空中传恨”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怀。因此,从时势的选择到雅词纯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词都符合朱氏的要求。
4.恪守词“别是一家”
朱彝尊赞同《花间》,追求词的醇雅,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词“别是一家”的准则。他努力将言情之词与儒家传统诗教相结合,而后又坚持诗词分工论。他在《紫云词序》中云:“昌黎之子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傲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晏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甚至认为:“今者兵戈尽偃,又得君抚循而照育之,诵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可偏废与?”他认为对于词而言,欢愉之辞,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辞,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词宜用于晏嬉逸乐,歌咏太平。朱彝尊此观点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后提出的,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宫廷唱和活动,提出文学为统治者歌咏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赓和,可以说歌咏盛世升平是康熙中叶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从对文学创作制约的角度上提出这一论点的,迎合了当时创作和审美的风尚。
朱氏的词学理论使清代词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指出的是,《草堂》是为歌妓应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观念,虽然如此,除掉柳永、康与之、胡浩然、黄庭坚的词后,大部分词仍是文人雅士之词,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对它的定位有失偏颇,导致他努力扭转明以来推重五代北宋词到专门推重南宋词。当然,朱氏所处时代是时人过分推重五代北宋词,词坛淫x的风气,他矫枉得需过正,将词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应该说时代选择了朱彝尊。事实上,朱氏本人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词及一味地排斥秩艳与豪放,他赞扬并推举《花间》便是例证。在他编选的三十卷本《词综》中,录人词数达l0首的词家中五代北宋便占了17人,而达20首词家中,以“俗”著称的柳永也占了21首,另外,朱氏在词中表达不喜欢辛刘的豪放词,而此书也收入辛弃疾词43首,仅比张炎少5首,人选作品包含了相当一部分辛词的代表作。他评价当时的词人,对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艳丽与豪迈特点也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江湖载酒集》被当时词人曹尔堪称为绵丽与豪宕兼而有之的作品:“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曝书亭集·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