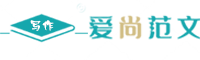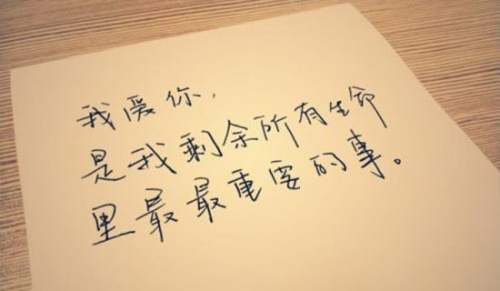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优秀6篇)
篇一: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古代文学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视角下研究古代文学,可以深入了解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以及社会背景,从而更好地把握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首先,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能够揭示出古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古代文学作为思想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例如,《孟子》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反映了古代中国人重视仁爱、正直、礼仪和智慧等美德。通过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代人们对于人性、社会秩序、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思考和追求,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其次,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揭示出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式、表达手法以及情感描写等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审美理念。例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而著名,通过研究其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对于自然、人情和生活的审美态度,进一步体味到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最后,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古代文学作为历史的见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通过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揭示古代文学作品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人们的思想和追求;通过把握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只有在文化视角下对古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
篇二: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取向,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在文化视角下研究古代文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首先,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能够揭示出古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古代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以及主题思想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例如,《红楼梦》中的“情牵于物,思丽于辞”等思想,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爱情、人性和命运等方面的思考和追求。通过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代人们对于人生、社会秩序、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思想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其次,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揭示出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式、表达手法以及情感描写等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审美理念。例如,唐代诗人杜牧的诗作以其简洁明了和深刻的意境而著名,通过研究其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对于自然、人情和生活的审美态度,进一步体味到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最后,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古代文学作为历史的见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通过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视角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揭示古代文学作品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人们的思想和追求;通过把握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只有在文化视角下对古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三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缺乏。古代,古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娱乐生活,很注重文学素养,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现象。因此,流传了数千年的古代文学还是能够适用于现代文明,甚至还是我国的文化魁宝和经典绝学,甚至有些经典作品被收录到教材中作为基础教学的素材。古代文学从神话故事和原始民谣开始,慢慢发展成诗、词、赋等带有韵律美和意境美的文学,然后逐渐形成小说、散文集等大规模著作。文化视角下,如何判断一篇古代文学著作是否经典,不单单考查作者的文学功底,还要去体会文学中作者注入的思想,这才是文学的灵魂,也是读者应该去研究的重点。从诗词歌赋到小说等古代文学著作中,有的抒发了心中对于美好大自然和浩瀚江河的喜爱之情,有的表达对于社会的讽刺以及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因此,笔者将古代文学分为几大类,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世俗与理想,桃花源的解读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借助路人偶然地迷失在桃花林,从而发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人人平等,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制度和肮脏的斗争。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理想的社会形式,但是“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的小人形象将作者拉向现实。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不管是官场还是社会都是黑暗的,导致他有才华而不能展现,有抱负而不能施展,因此愤然地离开官场,树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形象。在古代文学中,很多文豪通过文学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对社会制度的讽刺以及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类似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凄凉的心境。对于社会的黑暗制度的抨击,在每个朝代都是常见的,我们最为了解的就是《水浒传》中各路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桥段,林冲作为朝廷官员也迫不得已沦为草寇,这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制度和朝廷的。屈原遭受了黑暗势力的迫害,最后留下千古绝唱《离骚》而投江自尽。从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明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他们用绝美的诗句、文字筑造属于他们的桃花源。
二、凄美的爱情,悲凉的女性
爱情是诗人、艺术家手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浪漫的、多情的,同时也是凄美的。从古流传至今的爱情文学中,我们熟知的是牛郎与织女的神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千古绝唱,他们用生命去诠释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真谛。文豪用他们手中的笔将爱情的美好挥写得淋漓尽致,歌颂了心中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刻画了现实社会的黑暗。白居易的《长恨歌》让许多人愿意去尊重这段不伦之恋,同时也让读者为红颜薄命的现实而感叹,另一方面,这也是女性命运悲凉的体现。从古代文学上,我们可以知道有个为爱勇敢的女子卓文君,经过一番爱情的纠缠和背叛,最后写了《白头吟》与《诀别书》,这是她为女权,为爱情做出的斗争。另外,我们传诵的《红楼梦》正是爱情以及女权悲凉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贾宝玉和林妹妹的凄美爱情都让读者唏嘘不已,而《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这也正是曹雪芹本人在现实中体会的,毋庸置疑《红楼梦》是一部经典之作。文学是一种修养,它更是作者心中的一把利剑,能够直接刺中黑暗的要害,为爱情做嫁衣,为女性抱不平。
三、杜甫的情怀,人道主义情感
杜甫是一位诗人,爱国是其诗歌的灵魂,同时他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情人民,人们将其统称为杜甫的三大情怀。“自先君恕,预以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表达了他曾经也有雄心抱负,奈何仕途不顺,贫困与饥饿使他对穷苦人民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杜甫的爱国情怀也源于儒家文化和屈原的爱国情操对他的影响,使他形成了爱国“魂”,在“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感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在抒发对祖国的悲切之情的时候,还会赞颂祖国的大好山河,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包含了多少骄傲与自豪。杜甫也是为数不多能够为疾苦人民着想的伟大诗人,其代表作“三吏三别”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不幸,诗人从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而吾庐独破受冻死足矣”。正是这种悯人的爱国情怀,将他的诗歌作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影响他最大的就是儒家的“博爱”思想,促使他将人道主义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道家文化与李白思想
笔者认为李白的诗歌能够广为流传,不单单是由于其具有艺术性,还因为其诗歌包含深刻的哲学道理,而这来自道家文化对他的熏陶。李白的诗歌中反映了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朴素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思想,这造就了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情万丈的性情。其次他反腐朽统治,破弃礼法,同时他还消极厌世,追求及时行乐和访道求仙,这些表明了他与道家文化的联系是密切的。李白的诗歌磅礴大气,表达对秀丽山河的热爱,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黄河的咆哮描写得十分逼真。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写的多是水的豪情以及水的奔放,这和道家文化的《逍遥游》的思想很相似。庄子认为,大如鲲鹏,小如尘埃,都有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道家文化,一切顺乎自然,超脱于现实。因此李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熏陶已经贯彻到了他的诗歌当中,正是这种豪迈、洒脱的诗歌风格,他被众人称为“诗仙”。李白的诗歌充满想象和夸张,经常出现“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显”等寻道求仙的诗句,侧面表达了他以仙界的美好反衬世间的龌龊,而他求的不是仙而是他自己,这也是道家文化的色彩之一。
五、思乡情愫的寄托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很容易体会到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寄托的思乡之情,求学、战乱、迁徙等等都可能是思乡情愫的直接原因。思乡文学是古代文人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可以借助文人所处环境中的任何意象寄托文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在战乱不断的古代,由于统治者的愚昧和制度的黑暗,大多数文人有着怀才不遇的经历,他们不能在朝堂上施展才华,反而被发配到边疆去守卫边塞,面对浩瀚的边塞风光,文人心中的思乡情愫溢满心怀。《渔家傲》是范仲淹率领大军在西北平定西夏叛乱时所写,其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达了诗人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浓浓思念之情。同时,这也是一首很有争议的边塞思乡的诗歌,欧阳修认为诗人作为主帅不抒发豪情壮志,却去描写凄凉的边塞景象与思归之心,是不值得认可的。古代文人一般将月亮、杨柳、杜鹃、猿声作为意象来表达思乡情愫,杜鹃的别名和蜀帝杜宇的传说一直广为流传,诗人青睐借助子规啼来诉说思乡之情。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愁空山”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六、文人的人格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文学历史的开端,在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影响文人的人格,还深刻地重建着古代人文精神。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族文化的影响对于文人尤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文人在思想上的教育熏陶,使他们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力量以及人文精神,正是因为古代文学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精神,才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不息。同时,也正是正统的文学精神的引导,孟子的道家文化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思想,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陶渊明面对黑暗势力挺直腰杆,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愤慨,屈原在千古绝唱《离骚》中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美好愿望,面对迫害时奋不顾身投江自尽,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处就在于能够对文人起到正确的价值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让文人的人格能够在世俗中不被同化,还构建了一种超越体制的人文精神,对社会、对人民都有着同情和怜悯。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独特的魅力,同时这也是古人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我们要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肯定要先研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文学思维,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我们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领悟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真谛。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四
《古代文学习用批评范式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赵树功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该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结题成果,纳入宁波大学学术文库。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其相关思想、理论的论析范式与其思想、理论的论析具有相同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长河中得到坚持。难易论、压卷论、优劣论、正变论等就是被当下学术研究所忽略的古代文学批评习见范式。作为“范式”,它具有理论的集约性、基本内涵的传承性与方法的可操作性。“难易论”肇始于六朝,基本出于“尊体”的需要。“优劣论”从早期人物品目中衍生,在批评史上分别体现于作家优劣与作品优劣的论争。“压卷论”肇始于唐代的擅场论,是科举衡文在文学批评浸淫的产物。“正变论”出自《诗经》阐释之中汉人所谓的风雅与变风变雅的对立,随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关注的核心话语。
该书每个习见批评范式的研究包含以下基本层次:对其出处源流的梳理;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其在具体批评语境之中的表现;其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学精神本质。
《文明的悖论:约翰·密尔与印度》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耿兆锐博士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
约翰·密尔(John Mill,1806-1873)是 19 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逻辑学家、伦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思想体系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逻辑、伦理等诸多领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巨大,其自由主义学说在西方世界更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位西方世界公认的多才多艺的巨擘,是不列颠民族精神的象征,更被后人誉为“理性主义的圣人”。
作为国会议员,约翰·密尔整个人生职业生涯的 35 年都效力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担任高级官职,参与制定并决策了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各项事务。印度在约翰·密尔博大思想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记录历史的一般意义上来讲,都值得用心去探索和研究。
该著内容新颖,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拓宽了学界对于西方思想伟人约翰·密尔研究的新领域,弥补了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此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观、殖民观、文明观和东方观,也可为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妥善处理因文明差异所导致的分歧提供借鉴。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五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
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六
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幻境的美学特征
幻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境,是中国艺术中别具神韵的审美境界,尤以那些想象神奇、意动九天的诗歌和小说幻境最为集中地阐发了幻境美学之特征。
(一)非实冥空———意中之意、境中之境
中国山水画讲究以幻悟真,以幻启真。苏轼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主张在幻境中体验生命的真谛。幻境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艺术家心灵境界的呈现,它所描绘的情境要么借鉴于神话,要么发自于内心,不受时空的障碍,创造出一种现实不能出现或不能实现的人生过程。这种“意境”体现得最多的就是诗歌和小说。王维虽然以“田园诗”名扬天下,但在他的著名诗篇《桃源行》中,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蓝本,描绘了一处诡奇、梦幻的世外桃源。最擅长以“象”化“境”的诗人当属“诗鬼”李贺,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李贺诗“盖《骚》之苗裔,辞或过之。”认为尽管李贺诗中不少意象,“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但“求其情状”,例如在看他的《浩歌》中扪心拷问“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又说“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诗中各种意象应接不暇,有的采自神话传说,有的采自历史故事,有的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诗人将所有意象作了打破时空秩序的“蒙太奇”式的组合。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梦幻艺术的又一典范,众多想象的意象,亦幻亦真,使整部作品处于一个如幻如梦的境界之中,用一种浪漫的近乎神秘的笔调展示出人世的苍桑巨变,显示了人生中美的东西被践踏、被毁灭的现实,展现了一出女性和人生的大悲剧。青埂峰下的顽石既是这人生悲剧里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癞头和尚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借他们之口用一种荒诞的手法传达了对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感叹,以及饱经富贵与浩劫之后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豁达。
(二)即真即幻———行而无常、法而不空
中国传统之儒家,在学术思想上讲“经”讲“常”,以为天不变则道不变;但在立身治国上,则纯粹是针对人生生活面,所以讲仁义礼智信,讲诚正修齐治平,而不谈生前,不论死后,既无天国信仰,也不相信有来世,唯一确实掌握者为其现前自身之生命。这种观念,使中国人成为纯粹的现世主义者。然而岁月无情,现在转瞬即化为过去,万岁赓替,虽圣贤亦然。求长生而长生不可得,求及时行乐纵情声色而乐往哀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亦早有感叹: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曹子建的“天地终无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处处皆显示人生无常苦短之恸,故令霸气逼人的曹孟德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之慨。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根本上也就是通过贾府人物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的道理,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事,警幻仙子显示金陵因果名册,演唱十二曲红楼梦,暗示出生命的虚幻无常,与命运前定的因果观念: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巳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众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徼律;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述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三)不落有无———元而不盈、通透达心
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本土原也有类似思想,但却与佛家所云大相迳庭。大抵言之,儒家讲的是“天道福善祸淫”,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种将人事因果归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往往令人有一种天威难测、捉摸不着的感觉,故而对儒家此种说法的确实性与周遍性,颇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报思想则不然,讲的是生死轮回、三世业报。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从问来?死归何处?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对此问题,尚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论其余?而佛家轮回之说,非但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也为果报之说做了一圆满之答复,因为“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发展史上看出这种趋势: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梦来表达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识;用梦来承载他“千红一窟(哭)”、玉石俱焚的悲剧意识;用梦来寄托他怀金悼玉的泛爱意识,这三重意识,“构成了作者心灵广袤、深邃的、奥秘无穷的内宇宙”。
二、幻境之说的原始生命观
应该说,中国幻境之说或者说古代神话过早过多地被历史化,以屈原《离骚》中对于鲧描写为例,“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王逸注谓“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化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此应龙与禹的密切关系印证鲧化为龙的神话。另外,《天问》谓“伯鲧腹禹”,这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父子意义,甚至不仅仅是鲧的腹中生子的奇异,这是鲧的直接复活。不管是黄龙,亦或黄熊,还是禹,都是鲧的新生命。当然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继承鲧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龙与鲧初生时的称呼“白马”关联,《周礼夏官庾人》记“马八尺曰龙”,天马化龙,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来的应龙更是在治水中频频现身,透出鲧义不容辞的治水热情。它们属于鲧的生命图腾,而这图腾不是简单的崇拜或是奇异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观中,它们是“互渗”的。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的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中国神话中正包蕴着这种原始生命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轻易陷入神话历史化以后的许多“理性”解释而曲解神话的本意。如果说《离骚》中记载的神话仅仅是原始生命观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说则将这种原始生命观发展成熟。例如,《西游记》中一段“众僧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传说,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观中神秘的互渗律和生死循环、磨炼复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论,在《红楼梦》确实将这一思想诠释得最婉转曲折、深辟入里却又自然生动、逼真如实。例如在书中,通灵宝玉历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叹”的未用补天石,他与空空道人讲:“历来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这半生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反映、继承、传递了古人朴素的原始生命观,而这些智慧的感受,灵性的领略,也不仅仅属于原始人,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说的哲学渊源
儒家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而随着佛教东渡,佛教无常思想通过文人的彩笔,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结合,再搀和当时社会上道教的色彩,进而做了更深入、更彻底的探讨与发挥,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通过佛陀的睿智与高僧大德的西行求法,佛教的东传,带来了“万法皆空”、“诸行无常”的观念,这是何等的深入、彻底,而又是这样的震撼人心,非但更强调提醒原有人生苦短之观念,更充分地开拓刺激了中国人的哲学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无常不再只拘限于人生苦短之一点上,而趋于“诸行”无常、“万法”皆“空”上。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及清朝蒲松龄的《续黄粱》等,都是将人生数十年之种种遇合,浓缩到一场梦的短促时间内,来描写功名富贵以及人生之幻灭,如昙花一现,空而无常。如《枕中记》结段有言: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无生之情,尽知之矣。
自此,由唐诗宋词发展到明清小说,佛教“无常”思想对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吴承恩的《西游记》、陈仲琳的《封神榜》,还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特别是在《红楼梦》中,对于“一僧一道”和“经幻仙姑”、“太虚幻境”的描写,虽然篇幅不多而且写得恍惚迷离,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产生了特别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