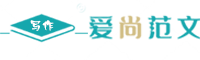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精选3篇)
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篇一
现实主义是一种追求真实、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流派,它以真实、客观、具体的方式揭示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而电影《驿站长》作为一部代表作品,也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
首先,《驿站长》通过真实而具体的叙事方式展现了社会现实。影片以一个小镇驿站为背景,通过描绘驿站长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影片中充满了生活的琐碎和细节,观众可以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场景,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真实的描绘使观众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对农村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驿站长》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影片中的驿站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勤劳朴实,为了维护驿站的正常运营,无私奉献。他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和原则。他是一个普通人的缩影,通过他的形象,观众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社会中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形象。这种对普通人的塑造,使观众产生共鸣,感受到了现实主义艺术所追求的人性的真实和尊严。
最后,《驿站长》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影片中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困、教育、医疗等。驿站长在片中积极为人民服务,尽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这种关怀和责任感体现了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社会责任和人道精神。
总之,《驿站长》作为一部代表作品,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通过真实、客观、具体的叙事方式展现了社会现实,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怀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这些特色使得《驿站长》成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艺术价值的作品,引起了观众对社会现实的深思和共鸣。

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篇二
现实主义艺术是一种以真实、客观反映社会生活为目标的艺术流派,追求揭示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真实性。电影《驿站长》作为一部充满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作品,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展现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
首先,《驿站长》以真实、客观的方式呈现了农村社会的生活场景。影片通过对驿站长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描绘,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观众可以看到农民的劳动场景、生活琐事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困境和挑战。这种真实的描绘使观众对农村社会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感受到了农民的辛勤劳动和生活的艰辛。
其次,《驿站长》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影片中的驿站长是一个普通农民,他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坚守自己的职责和原则。通过对他内心的独白和情感的表达,观众可以深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这种对人物内心的描绘,使观众更加贴近人物,对他们的情感和命运产生共鸣。
最后,《驿站长》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影片中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困、教育、医疗等。驿站长在片中积极为人民服务,尽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体现了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社会责任和人道精神。观众通过影片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描绘和反思,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的需求。
总之,《驿站长》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作品,通过真实、客观的叙事方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展现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观众通过这部电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农村社会的生活,感受到现实主义艺术所追求的真实和人性的复杂性。
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篇三
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摘 要:《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开山之作,普希金成功地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 “小人物”。此后,俄国现实主义的作家们竞相将这一主题发挥到极致。本文试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手法的探究来揭示其其中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现实主义; 典型性; 人民性; 悲剧性; 浪漫主义;职称论文
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反映现实,描写现实的文学,它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俄罗斯文学特有的色彩: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洞察人性,以期引导和改造社会成为俄国历代作家的光荣使命。正因为此,在19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并最终跻身世界伟大文学之列。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中已经成功地反映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和艺术要求。
一、典型性
典型性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物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1]。。不仅人物有典型问题,环境也有典型问题。
“连续二十年,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2]通过这段抒情议论,作者高度概括了像驿站长这样的下层人民在俄国不计其数,而作者对他的典型化塑造,有利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在第一次到达驿站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有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通过这个典型环境可以看出,维林和女儿冬妮娅过着安详和幸福的生活,而此时的主人公维林也“五十来岁”,但“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 “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通过对父女俩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父亲为有人见人爱的女儿而如沐春风,而年幼的冬妮娅虽然美丽动人,但其长期所处的环境把她过早地催化成一个性心理早熟的姑娘,俨然失去了十四五岁少女该有的那种纯真,在此作者除了对冬妮娅以后生活道路的选择做了铺垫以外,还暗暗地谴责了那个可恶的社会。
在与父女依依惜别之后的若干年,“我”又由命运带到了这所驿站,当我重新踏进房间时,“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景象”今昔对比如此强烈怎使人不心生悬念:究竟发生了什么?而看到驿站长“花白的头发,望着他那好久没刮胡子的脸上深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会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衰弱的老头。。在通过维林的讲述,我们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了爱女被拐,寻女被驱单位整个过程。
而“我”第三次故地重游又是过了许久之后,此时的驿站已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而“我”也几乎要欲语泪先流了。 “四周光秃秃的,毫无遮拦,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这是可怜的维林艰辛一生的最后归宿,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俄国下层小人物的悲惨一生,激起了读者的无限悲悯和同情,达到了悲剧的艺术目的。
二、人民性
一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作家们从不间断地描写俄国社会现实,反映俄国人民疾苦的苦难史。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文学要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他们的贫穷和烦忧,同时也要正确表达出人民的美好和力量。”[2]作为贵族出身的普希金能够在19世纪30年代抛弃其阶级的局限而与普通大众站在一起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也成为他是俄国现实主义奠基人的有力凭证。他的作品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
他的创作已全然不同于18世纪罗蒙诺索夫式的对沙皇统治者的颂歌式的赞扬,更不同于卡拉姆辛在《苦命的丽莎》中感伤的叹息,而是积极地暴露了身处底层的维林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苦难境遇。但由于普希金所处的时代还不是俄国最黑暗恐怖的阶段,所以维林悲剧性的人生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性格中的缺陷。
作品中的人民性不光体现在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更重要的是整部作品中深深浸透着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同情,充满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借“我”在省长的晚宴上受到了仆人的冷遇,和驿站长在接待来往旅客时所受欺辱的同命相连,呼唤人们对下层小人物要有一颗同情心,倡导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关爱,尊重人性,这种博爱之情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正是出于这种全人类的博爱精神,所以《驿站长》中围绕着谴责明斯基的巧取豪夺致使维林失去精神支柱外,也从人性角度作了立体的'思考,似乎维林,冬妮娅,明斯基每个人都有错,但每个人所作所为似乎也都有合情合理的方面,并非是罪不可赦的。所以这种纠结的冲突为作品获得了悲剧性的效果,这种冲突不光是社会的,也是人性亘古就有的冲突。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父亲的维林理所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女儿,避免

19世纪是俄国文学开始真正发轫的时代,作为现实主义奠基人的普希金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保留了浪漫主义的痕迹,如较多的主观抒情。这直接导致的是作者的感情过于外露,与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契诃夫的作品的含蓄相比确实缺乏深度,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
结语:普希金的《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的这种开创性为后来的《谁之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提供了哲理性的思考话题。在他之后果戈理笔下的《外套》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虽各具特色,但都继承了普希金创作中的光荣传统。
参考文献:
[1]Е Е Сокрутенк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 》,1965 г.
[2]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4.
[3] [4]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普希金.俄国短篇小说选[M],水夫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